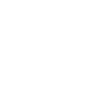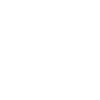文献悦读 | 法国大学组织变革研究(一)
摘要:由于历史原因,法国大学治理模式具有中央集权和学术团体“双重集权”的特点。20世纪80年代末,新公共管理改革深刻影响了法国高等教育的行政和组织模式,新的预算组织法、大学自治法、大学合并等政策及措施都进一步加强了校长责任制、绩效、质量等理念,削弱了传统上的学科组织逻辑。虽然法国大学变革的趋势在全球化背景下也受到同质性的质疑,但穆斯兰等学者的结论仍是支持本土化模式的探索与建构。全球化的未来并不明朗,大学在追求国际能见度的同时,更应该回归高等教育的本质,并更多地承担国家责任。
关键词:法国大学 、新公共管理 、教育全球化、大学组织变革、大学合并
大学一直是组织社会学家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中世纪大学起源于法国,其最早确立的大学理念深刻地影响了现代大学的发展。19世纪初,拿破仑建立“帝国大学”,确定了法国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模式,从组织的角度上讲,大学已经被消解,只剩下“学院共和国”。[1]1968年,《高等教育方向指导法》(“富尔法”)重新确立了大学自治、参与和多学科的组织原则,法国才走上了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之路。法兰西组织学派代表人米歇尔·克罗齐耶 (Michel Crozier) 曾指出,产生于 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组织社会学理论并不能对法国的社会现状作出说明,法国社会学界需要一种新的组织理论,在高等教育组织研究领域,克罗齐耶的弟子克里斯蒂娜 ·穆斯兰 (Christine Musselin)无疑是欧洲范式的代表。本文从20世纪末期穆斯兰建构的法国大学组织特点出发,论述了高等教育国际化和新公共管理对于法国大学组织发展造成的影响,总结了法国大学近些年呈现的新的发展特征和趋势。
1.法国大学的组织特点
穆斯兰在《寻找大学:法、德两国大学的比较研究》(En quête d’universités: étude comparée des universités en France et en RFA)(1989)、《法、德两国大学的正式化组织结构及其整合能力》(Structures formelles et capacités d’intégration dans les universités fran aises et allemandes)(1990)等一系列成果中细致考察了法国大学的内部组织模型和外部治理关系。与克罗齐耶相比,穆斯兰的视角更偏向于组织内部的行动,也更关注组织内的个体。
教师—研究人员是法国大学组织内最核心的个体,但学术工作个体化的特征使得大学教师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很弱,各自划分科研领域的意愿又强化了这一特征。[2]弱的人际关系又造成教研单位内部四分五裂,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小团体,每个小团体内部又展现出可能进一步被分化的倾向。传统遗留下来的法国大学的学术自由,为组织内部的教师—研究人员独立寻求各类支持提供了可能,特别是这些个体可以从外部(国家机关、地方行政区域、研究机构、基金会和企业)争取到资金和合法性的支持。当然,大学组织的存在离不开内部的行动者,因为行动者是唯一的系统支撑者,是唯一能赋予系统生命,并且能让系统发生变化的要素。[3]所以,教师—研究人员之间疏离分裂,亚组织各自维持张力,大学与教师—研究人员之间若即若离又唇齿相依,成为法国大学的隐性组织文化。

穆斯兰认为,大学亚组织的规模和数量在不同学校内部各不相同,但无论如何,以教研活动为中心的小型教学及科研单位都处于法国大学的中心位置,集中了同一学科或专业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因此,从理论上讲,教学及科研单位就是法国大学最基层的组织单位,但事实上,这些单位内部又产生了无数个正式或非正式的小群体组织。这些小群体组织不存在强有力的功能性依赖关系,却形成一种有效分离,即教师和研究人员能够以其身处的组织为屏障,减少与其他学部、院系或实验室成员的合作。[4]在这里,不同的小群体组织几乎扮演了一样的角色,即把不同的学科进一步分化,使得学科知识朝着更加专门化的方向发展。同时,小群体组织在学科之间还建立起了难以打破的壁垒,这些壁垒反过来又恰好成为学者们维护自身独立性的保护屏障。
通过对德国大学和法国大学的组织特征比较可以看出,德国大学的自治程度高于法国的大学,德国大学教师的归属感和组织忠实度也更强。[5]可以从两国教师聘用制度为例来说明这种差异:
在法国,由于历史原因,大学内部基层单位的权力很大,专业性也很强;在教师聘用过程中,专家教授的话语权有着绝对影响力;决策程序往往只是形式,对于大学组织的整合作用非常小;上层机构也不会反复认真研讨提议,基层组织的建议就是决议。高度的专业化赋予了法国大学教学与科研单位极大的权力,大学领导层能够发挥的余地很小。但是,法国大学各个基层单位之间的关系比较松散。法国大学决策机构在选举时往往充满着政治冲突,只不过在平时运行过程中显得一团和气,机构内部成员的到场和维护各自利益远远胜于他们在参与集体决策过程时所做出的努力。[6]
德国大学的决策过程则表现出循环性和持续性。大学决策机构在运行上更加严密,每一项建议都会得到认真审议,并且决策代表都能够积极承担责任,也不会把决定权轻易交给他人。大学对决策过程也进行全程监督,督促每个参与者遵守规章制度。学校整体的决策机制塑造了学校的话语权,与法国的模式俨然相反。当然这不代表德国大学内部学科之间是和谐的。事实上,德国不同专业和个体之间在人员招聘、教学科研等工作中的竞争屡见不鲜,只不过,在德国大学内部即便存在个体微弱的意志,但最终仍然能够形成共同的价值并支持大学采取共同的行动。
2.高等教育全球化与法国大学的合并浪潮
近些年来,世界主要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都经历了快速而深刻的变革。虽然民族国家的特征依然明显,而各国改革的原则和特征又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7]可以看出,高等教育的全球化不仅极大地便利了师生流动、学术交流、科研合作,同时促进了各国建设大学经验的相互比较和借鉴以及国际大学评价体系的建立。作为高等教育先发国家,“法国大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和良好的教育传统,然而在世界大学排名中的表现却差强人意”[8]。学界普遍认为,法国大学小而散,大学层面缺乏领导力,教育与研究单位之间壁垒横亘,科层制度导致管理效率低下,跟不上时代发展,从而导致国际能见度低。大学合并似乎成为一条简单易行的道路,因为合并不仅可以增加人员数量,有利于重新洗牌打破学科界限,受到国家重视,特别是可以提高大学的国际排名,得到世界的关注。
法国率先开展合并的是位于北部德法边界的斯特拉斯堡大学。今天的斯特拉斯堡大学是由过去的斯特拉斯堡一大、二大和三大三所大学合并而成的。过去的斯特拉斯堡一大以自然科学见长,学生最多,实力最强 ;二大以人文学科为主 ;三大则偏重于欧洲问题的研究,法律和管理专业较强。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法国中央政府为了提高国家研究创新能力,就开始鼓励传统上三足鼎立的大学、“大学校”和科研院所展开合作。教育部鼓励区域内的高校和研究机构组成松散却相关联的“联盟”“集群”或“中心”,促进人员流动和资源共享。在此框架下,斯特拉斯堡三所大学开展了多项合作,然而毕竟各校法人主体不同,复杂的行政管理体系导致了决策效率低下,为此合并为“完整”、“巨型”、“有力的治理”的大学 [9],真正促进资源优化共享和跨学科项目建设,提高国际竞争力,成为三校合并的初衷。“完整”即学科的完备,如前所述,斯特拉斯堡的三所大学各有所专,学科配置各有千秋,虽然教学和科研的合作既不缺乏内驱力也非欠缺外部政策,但组织结构却成为障碍。学科的完备不仅有利于学生开阔视野,也有利于促进跨学科研究,而且有研究结果显示,跨学科的文凭在欧洲就业市场上受到欢迎,学生更具有竞争力。学科完备的综合大学也更容易在国际上得到认可,更有机会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大学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而且国际排行中也常常会把学科的完备以及国际化的程度作为评价的重要指标。三所大学统一以斯特拉斯堡大学的身份亮相世界,既能作为这座城市的知识界代表,展现整座城市的发展风貌,又能提高外在可见度、促进内部成员的整合。
合并后,法国大学的组织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首先就是以校长为代表的校级层面权力的增强。长期以来,法国大学一直受到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和学术寡头为中心的学者社团的双重限制,大学层面力量薄弱,校长身份尴尬。而合并作为改革的契机,推动了校长责任制的治理转型。穆斯兰将促进合并的三位大学校长称为“行动团队”,并将其描述为新公共管理中的“机构创业人”:他们既不是在执行国家政策,也非头脑发热的改革家,而是“机构的创业人”,具有很强的“能动性”。校长们的创意推动了一项创新性的制度,实现了自下而上的变革。他们作为科学家和国际学者所拥有的视野使他们一直坚信,建立一所完整的大学,将所有的力量集中在一起才是大学发展之佳径,否则,大学将失去未来。[10]
合并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酝酿,还有权力地位关系的博弈。对于斯特拉斯堡一大来说,提高大学的国际可见度,适应欧洲乃至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是驱动其倡议合并的出发点。而斯特拉斯堡二大和三大当时的学科设置、人员配置、经费资金都不足以将发展提高到国际的高度,能够在法国国内生存下去已经不易,所以后两者的选择更多是出于自保。二大的领导层认为,人文社会科学只有在自然科学的保护下才能够得以生存......只有实力相对强大的大学才会为人文社科提供更强有力的保护[11],而三大为了不被孤立,则选择了妥协。
对于强势的一大而言,大学的合并带来的更多的是国际影响力和更强的外部身份认同,其组织文化和组织行为方式基本可以得到保留 ;而对于二大和三大而言,虽然面临被同化的危险,但其本身的学科的确在完备巨型的大学中得到了保护。正如穆斯兰曾描述的,信仰和对合法性的追求并不是高等教育神话得以传播的唯一动力 :在危机中寻求地位自保或者出于被甩在身后、被孤立的恐惧都可能导致立场的转变。[12]
参考文献:
[1][6] Christine Musselin. La longue marche des universités fran?aises[M]. Paris:Puf,2001:43,62.
[2][4][5] Christine Musselin. Structures formelles et capacités d’intégration dans les universités françaises et allemandes[J]. Revu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 1990: 31-3.pp. 439-461.
[3] 米歇尔·克罗齐耶、埃哈尔·费埃德伯格 . 行动者与系统 [M]. 上海 :张月等译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17:21.
[7][9][10][11][12] Christine Musselin, Maël Dif-Pradalier. Quand la fusion s’impose : la (re)naissance de l’université de Strasbourg[J]. Revu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 2014, 2 (55):285-318.
[8] 刘敏 . 世界一流大学的管理及制度建设——巴黎十一大为例 [J]. 比较教育研究 , 2011 (5):36-40.
作者:
刘 敏,女,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副教授
王丽媛,女,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 声明:本文由协進教育编辑整理自《比较教育研究》2018年第8期总第343期,版权归原著所有,如有疑问请联系13917844460。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复制链接
复制链接